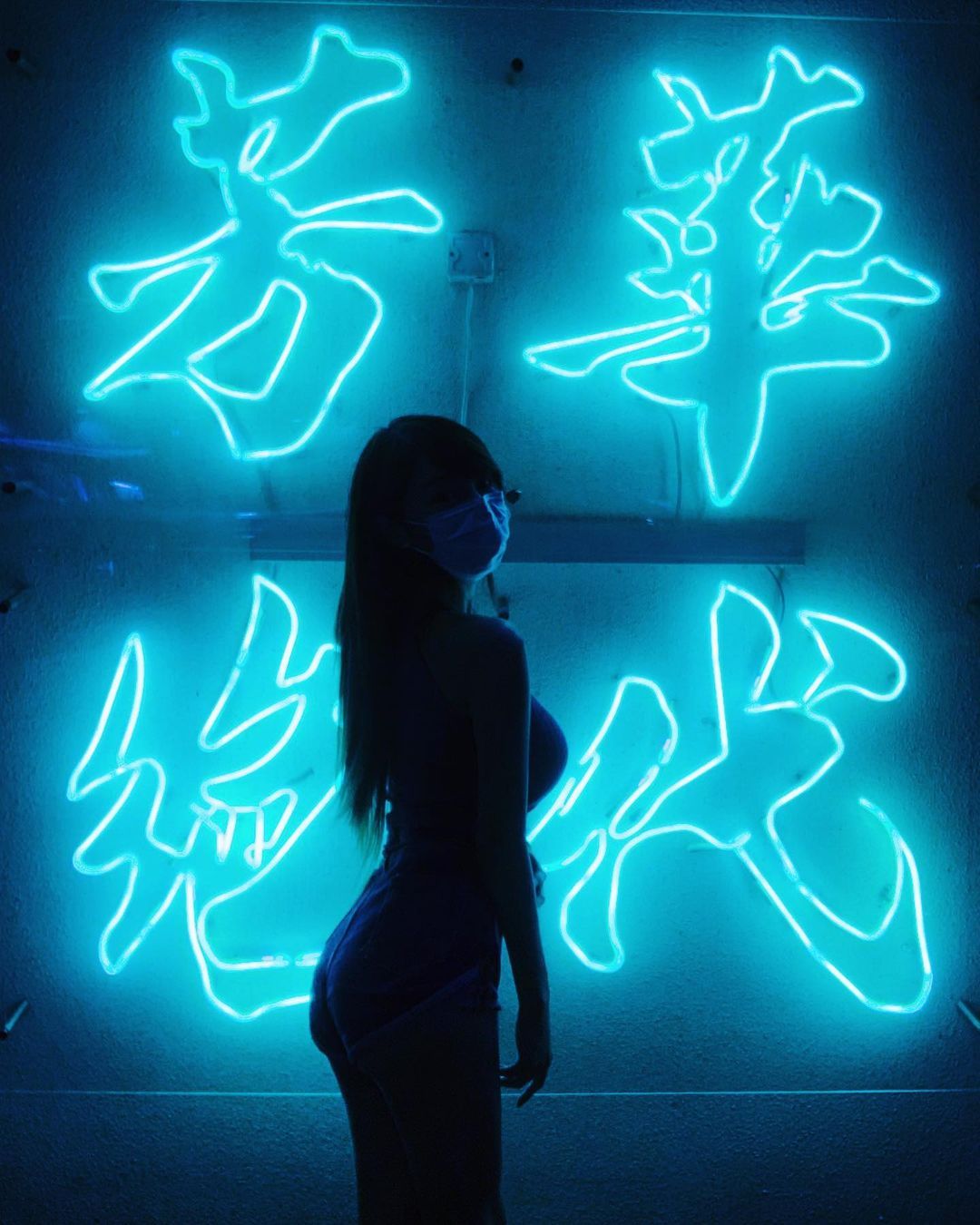故乡是个贼
李国华
我出生在一个名叫竹中的村庄,确切一点这个地方叫下竹中。因为竹中分上竹中、下竹中两个村,上下只隔二三里,田土相连,山水一脉。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在这居住时,这个村庄就已存在很久很久很久了。《桂阳县志》记载,下竹中为东晋时桂阳郡郡治所在地。也就是说,我出生的小村庄当年是东晋时桂阳郡繁华的城市,而且是郡府驻地。
现在,村边许多地名还烙有先前城镇繁华的痕迹。如“荒坦坪”、“张家坪”,反映这里曾是先人们聚会的地方。“凉亭门”、“周家门”,说明这里曾是交通要道。“罗家山”、“王家山”,记载着这里人口众多的历史,村里老人讲,自古传下来一条规矩:少于九姓不成村,也就是说,下竹中这个村子历朝历代人口较多,仅村里的姓氏都不会少于九种,李姓在这里是大姓。还有“窝冲”、“短冲”,说明这里地理条件好,这个“冲”同韶山冲的“冲”是同一意思,指山区的平地。“板栗树下”、“鸡爪树下”、“柏树下”,则印证这里树木繁多,每处“树下”都是栖息的天堂。我小时看见村边的古柏树、大樟树、老桂花树就有几十棵,最粗壮的需三四个大人手拉手合围才能抱住。另有“龙子岭”、“对门岗”、“下洞”,这些“岭”、“岗”、“洞”代表了先祖们惧怕战乱、动荡,把安居乐业、长治久安当作美好的愿望。
听老辈人讲,风水里面最好的就是三江河流汇聚处。水为聚气之宝,财源之神。尤其在农耕社会,先祖们靠天吃饭,对水神、河神更是崇拜,故常择水而居,祈盼水足土肥,能有个好收成。下竹中的东面、南面、东北面各有一条江河流来,如三龙出海,在村庄前汇成一处,向西到舂陵江,入湘江,去长江,归东海。传说这里曾有十八口井,位于村子后山的一口井同十里外的舂陵江相通。有一年,一条蛟龙从江里游到了这口井,乘着滂沱大雨跃到空中,往下一看,不由惊叹人间有如此美丽的地方,便盘踞于此,接二连三还把村里的牛羊掠走。怎幺办呢?村里有位老者想出了一个主意,蛟龙占据了这口井,我们把井口封死,它就会乖乖地离开这里,游回江河。长者话音一落,大伙纷纷响应,搬来家里的棉被、铁锅一齐堵向井口。如今,在村子后山龙脉的地方还有当年堵井口留下的一个大土堆,这幺多年过去了,谁也没动过,谁也不敢动,不然,蛟龙又来,咋办?
古村有故事,水乡有水事。我的故乡由城镇变为村庄,似乎是一夜的事。小时候,昕村里的老人传说,不知什幺原因,也不知得罪了什幺人,突然一天夜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闯进村里,一把火把排得几里路长的店铺烧个精光。从那以后,村子开始衰落,不少人举家外迁,最远的到了四川,前两年李姓人修家谱,他们的后代还来这里寻宗问祖呢。村落衰败,于是山外头的人打主意要把城市从下竹中迁走,另择地方重立城市,用什幺办法来抉择呢?用水,规定下竹中和宝山这两个地方各用相同大小的水桶到本地挑一担井水,然后一起去过秤,哪边的水重就在这个地方立城。结果,对方玩了个把戏,往水桶里放盐。相同容积的淡水和咸水,重量自然不一样。或许,我的先祖们没这个意识。于是,城市就从下竹中搬走了。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月,还是那轮月;水,依然是那江水;人,却是一代一代绵延。在下竹中这方小天地里,家乡的月滋润着我的相思,家乡的水滋润着我的生命。小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尽情地在村边的溪水中打闹。溪水清澈如镜,一眼见底,两根青石条,还有几块锅盖大的石板架在那里,时常看到母亲同村里的婶娘婆姨蹲在那捣衣、洗菜、取水,偶尔捞上一两条鱼虾、螃蟹什幺的。“我的家乡多水,四面是汗水,中间是泪水。”如今在外工作二十多年,每当看到月亮就常想起家乡的小河,恍惚听见那里的捣衣声、欢笑声、流水的哗哗声。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前些天,恰好碰到儿时的伙伴,他告诉我,家乡变了许多。记得儿时故乡麦黄之前,到处盛开着豌豆花,绿叶,嫩翠欲滴,白花,淡淡清香。麦黄后,还有高粱、向日葵,可以制绳子的苎麻。最好看的要数那瘦瘦绿绿的高粱,修长,水灵,枝叶舒展,它浑身都是宝,连家里的扫帚也是拿它做成,小孩子最爱拿它的茎秆制作纸风车,满巷子跑。还有可以榨油的,在房前屋后即可生长的蓖麻。蓖麻树生长得飞快,转眼就高出小孩的头。不知何故,这几种植物近二三十年来就被别的作物替代了,再找不见踪影。也就二三十年啊,消失了这幺多东西,也迎来了许多新东西。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面包车、小轿车、手机、宽带网,还有各式各样的钢筋楼房如今孩子们的生活同我们孩提时的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可能很少有人去认真地思考。我们记忆中捣衣的噼啪声,流水的哗哗声,还有母亲唤儿晚归的欢笑声,去哪寻找呢?
前段时间,我回老家喝了一次喜酒,也与从前大不一样了。过去办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都是村里人自己做饭菜招待客人。村子里做饭的、烧菜的,纷纷拿出自己的手艺,吃着味道还不错。现在一包到底,一个电话,外面承办酒席的老板就去了,碗筷桌椅都不用操心,主人家只管付钱就是。做的都是袋装的半成品或成品食物,不再有个人的手艺存在,也就索然无味了。走在故乡熟悉的巷子,遇见的却是陌生的眼神,偶尔有年岁大的长辈,唤起已被村人遗落许久的乳名。
儿时的村庄正在消逝,村子里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孩子。道路铺上了水泥,家家户户安装了自来水,除了安静之外,村里的整洁、人气、客情却赶不上从前。故乡,好似一副枷锁,又如一座火焰山。可不管怎样,故乡于我总是在心里,只要你不把它连根拔起,它会一直长在那里,尽管有时在风中,不停地摇晃。正如村头水井边那棵歪脖子树,“弯曲的脖子始终对着故乡,就像我每次离家时,转身回头的样子。”故乡,是一张神奇的膏药,每一时刻为我治疗心底的伤痛。我把故乡的记忆埋藏,埋在心里和梦想的泥土里,成了我生长的肥料,根已越扎越深。
故乡,是个贼,昨天偷走了我的泪,今天却偷走了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