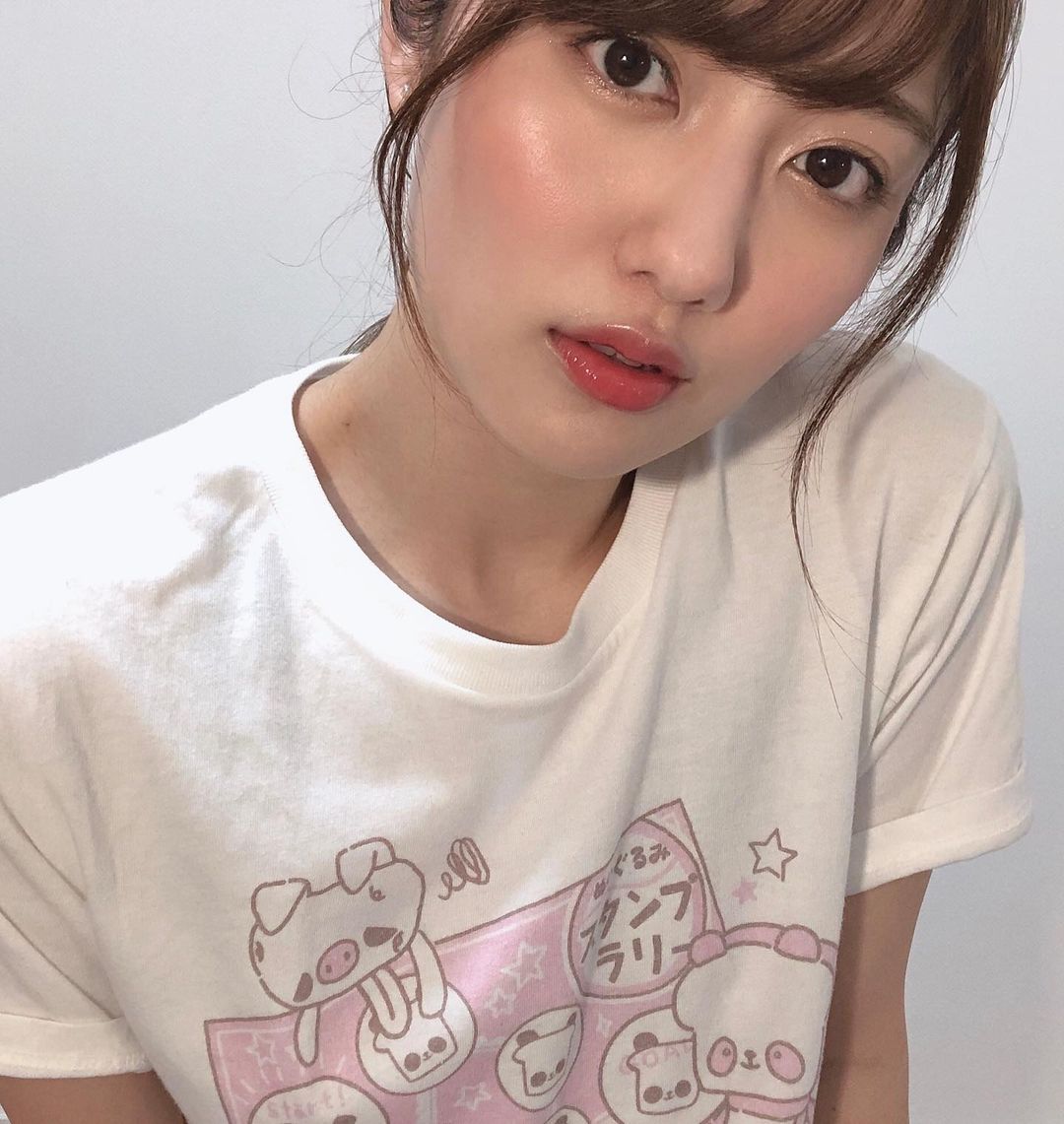石棺
“咱们做笔交易如何?”我拍了拍方才的后脑勺。
“我不和你这种人做交易。”他企图挣扎一下,“快把小雪还给我!”
“事到如今,你为什么不能放弃那些无聊的原则,务实一些呢?”我温言相劝,“你看这地方,多么理想,咱们尽可以互相说些出我口入你耳的话。”
他愣了愣,“互相?”
“是的,你说一件,我说一件,大家互惠互利。离开达哈苏后彼此概不认账,很公道。”
方才沉思着,眼珠转来转去,考虑其中的利害关系,最后他慢慢地点了点头。
“你做了明智的选择。”我满意地点点头,“你先问,以示我的诚意。”
“你把小雪藏到哪里了?”他迫不及待地问。
“这个问题除外。”我讥讽道,“就算我告诉你了,又能怎么样?你有本事制服我吗?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她活得好好的。杀了她对我没好处,信不信由你。”
我没有骗他,假如那个护林员要杀薛晴雪,趁黑给她一刀即可。尽管我不清楚挟持的目的,但抓牌是为了打出去,而不是撕掉。至于对方何时出牌,只能静观其变。
他满脸沮丧地垂下头,过了半晌,低声道:“我和你见面时提到的那起车祸,是不是你策划的?”
“策划这个词并不准确,我从来不给客户提供详细的计划,我只是给他们一个灵感,具体怎么办得靠自己去领悟。如果连基本的领悟力都没有,那种蠢货最好远离为妙。”
“能说的具体些吗?”
“该我问了。这个女人为什么带你来这里?”
“……你带走小雪时,我听你提到净水湖。来达哈苏之前我研究过地图,知道它的位置,等你走后,我跟了过去。在静水湖边遇到了她。她自称是赵小树的母亲,听我说了前因后果,愿意帮我找到你,救出小雪。我想不出她有骗人的理由,便跟她来了。”
“你怎么没报警?”我似笑非笑地问。
“***没人,手机没信号,城里的人像是都死了,不管我怎么敲门也没人搭理!”
的确,达哈苏的夜晚一直是这般模样。
“那起车祸的灵感很简单。人在长时间不沾油腥后,一下摄入油水很大的食物,必然引起腹泻,即便检验出来也算不得证据。”
“我明白了。”方才恍然大悟,“买通那个老妇人的私人医生,找点理由让她戒口,然后安排宴席邀她参加,那地方比较偏僻,回来的路上设下圈套,利用她腹痛难忍不及辨认……出事的地点是盘山路的急转弯……你们在那里布置了什么?”
“你和那个女人走的哪条路?”
“是乘车而来。净水湖北面的山中有个隐蔽的隧道,隧道口有辆破旧的客车。车无法发动,都睡了一觉,她才修好。那条隧道很长,开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这里。”他闭了嘴,紧紧地盯着我。
我无奈地耸耸肩:“一个女孩事先打扮成老妇人外甥女的模样,站在那里。她魂飞魄散,为了躲避,车翻下了山。”
“……她的外甥女五年前死于意外,照你这么说……是她杀的?……原来如此,她做贼心虚,杀害外甥女后处处小心事事留意,连别人家的厕所都不用。那是场自助餐,她放心地参加了,感到肚子不适后提前退场……原来这不是谋财,而是复仇。”方才两眼发光,喃喃自语。
我不动声色地端详着他,心里思量另一个问题:隐蔽的隧道,破旧的客车,死去那个女孩留下的客车票,三件东西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线。
只是一条线,不是一个环,还缺少某种关键性的连接。
我蹲在女人的尸体前,她两眼翻白,满脸惊愕。撩开她的头发,额头上有一片烧红的疤痕。
没错,是她,达哈苏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她是那座城市对我最温柔的一个人,但她自己的日子并不顺心。作为被上级指派来的外乡人,无论付出多少努力,换来的始终是冷漠和提防。风华正茂的女孩,在忽如其来的一场大火中身负重伤,从此销声匿迹,待到我再次与她重逢,尚未谋面便死于非命。
可惜,不知是泪腺先干涸,还是心肠变得冷硬,百感交集,仅化作一声叹息。
“你是怎么向她介绍我的?”我问方才,“称我为某先生?”
“……我告诉她,你是个流亡的歹徒。”
“流亡?这个词挺好。”我摇摇铁锹,它被头骨卡的很紧,看上去正是因为如此,方才捡了一条命。
“带我去看客车和隧道。”我转身走到方才面前。
“我还有问题。”他抗议道。
“交易时间结束了。”我踢了他一脚,“快起来,带路!”
他磨磨蹭蹭地站起身,“你走前边,我怕你背后暗算。”
我哑然失笑,“有区别吗?我要真想动手,你骑在我脖子上也没用。只要你不耍花招,我保证不伤你性命。”
我和他各怀心思,闷头行走在浓雾中。
达哈苏广播电台的频率是83.1,虽然它仅维持了两个月,但我依然记得每天傍晚五点半那个天使般的女声:“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节目,首先播放的评书联播……”
有限的半个小时,是我儿时最快乐的时光。我贪婪的趴在训导处的桌子上,不愿遗漏评书的每个字,每晚躺在床上细细回味。直到有一天,收音机响起一段美妙的音乐。
小号悠扬,旋律如梦似幻,我听得陶醉不已,忽然音乐中断了,一只手粗暴地关掉了收音机。我想要打开,结果被毒打一顿,整整躺了三天。
很久之后我知道了那段音乐的名字:月亮河。